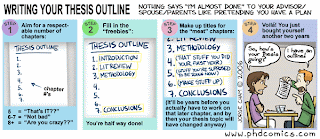這是一篇關於爸爸的文章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龍應台/如果當他垂垂老時,他可以回鄉了,山河仍在,春天依舊,只是父母的墳,在太深的草裡,老年僵硬的膝蓋,無法跪拜。鄉里,已無故人。他一上來我就注意到了。老伯伯,留著平頭,髮色灰白,神色茫然,有點像個走失的孩子。裹著一件淺褐色的夾克,一個皮包掛在頸間,手裡拄著柺杖,步履艱難地走進機艙。其他的乘客拖著輪轉行李箱,昂首疾步往前,他顯得有點慌張,低頭看自己的登機證,抬頭找座位號碼。不耐煩的人從他身邊用力擠過去,把他壓得身體往前傾。他終於在我左前方坐下來,懷裡緊抱著皮包,裡頭可能是他所有的身份證明。柺杖有點太長,他彎腰想把它塞進前方坐椅下面,一陣忙亂,服務員來了,把它抽出來,拿到前面去擱置。老伯伯伸出手臂,用很濃的甘陝鄉音向著小姐的背影說,「要記得還給我啊。」
我低頭讀報。
台北往香港的飛機,一般都是滿的,但是並非所有的人都是去香港的。他們的手,緊緊握著台胞證,在香港機場下機、上機,下樓、上樓,再飛。到了彼岸,就消失在大江南北的版圖上,像一小滴水無聲無息落進茫茫大漠裡。老伯伯孤單一人,步履蹣跚行走千里,在門與門之間顛簸,在關與關之間折騰,不必問他為了什麼;我太知道他的身世。
他曾經是個眼睛清亮、被母親疼愛的少年,心裡懷著鶯飛草長的輕快歡欣,期盼自己長大,幻想人生大開大闔的種種方式。唯一他沒想到的方式,卻來臨了,戰爭像突來的颶風把他連根拔起,然後惡意棄置於陌生的荒地。在那裡,他成為時代的孤兒,墮入社會底層,從此一生流離,半生坎坷。當他垂垂老時,他可以回鄉了,山河仍在,春天依舊,只是父母的墳,在太深的草裡,老年僵硬的膝蓋,無法跪拜。鄉里,已無故人。
我不敢看他,因為即使是眼角餘光瞥見他頹然的背影,我都無法遏止地想起自己的父親。父親離開三年了,我在想,如果,如果再給我一次機會,僅僅是一次機會,讓我再度陪他返鄉──我會做什麼?
我會陪著他坐飛機,一路牽著他瘦弱的手。
我會一路聽他說話,不厭煩。我會固執地請他把他當年做憲兵隊長的英勇事蹟完整地講完,會敲問每一個細節──哪一年?駐紮在鎮江還是無錫還是杭州?對岸共產黨勸你「起義」的信是怎麼寫的?為什麼你沒接受?……我會問清每一個環節,我會拿出我的筆記本,用一種認真到不能再認真的態度,彷彿我在採訪一個超強大國的國家元首,聚精會神地聽他每一句話。對每一個聽不懂的地名、弄不清的時間,堅持請他「再說一遍,你再說一遍,三點水的淞?江水的江?羊壩頭怎麼寫?憲兵隊在廣州駐紮多久?怎麼到海南島的?怎麼來台灣的?坐什麼船?船叫什麼名字?幾噸的船?砲有打中船嗎?有起火嗎?有沒有人掉進海裡?多少人?有小孩嗎?你看見了嗎?吃什麼?饅頭嗎?一人分幾個?」
我會陪他吃難吃的機艙飯。我會把麵包撕成一條一條,跟空中小姐要一杯熱牛奶,然後把一條一條麵包浸泡牛奶,讓他慢慢咀嚼。他顫抖的手打翻了牛奶,我會再叫一杯,但是他的衣服不會太濕,因為我會在之前就把雪白的餐巾打開鋪在他胸口。
下機轉機的時候,我會牽著他的手,慢慢地走。任何人從我們身邊擠過而且露出不耐煩的神色故意給我們看,我會很大聲地對他說,「你有教養沒有!」
長長的隊伍排起來,等著過關,上樓,重新搭機。我會牽著他的手,走到隊伍最前端,我會跟不管那是什麼人,說,「對不起,老人家不能站太久,您可以讓我們先進去嗎?」我會把他的包放在行李檢查轉輪上,扶著他穿過電檢拱門。如果檢查人員說,「請你退回去,他必須一個人穿過」,我會堅持說,「不行,他跌倒怎麼辦。那你過來扶著他!」如果不知為什麼,那門「逼」一聲響起,他又得退回,然後重來一次,我會不管三七二十一,牽著他的手,穿過。
當飛機「碰」一聲觸到了長沙的土地,當飛機還在滑行,我會轉過身來,親吻他的額頭──連他的額頭都佈滿了老人黑斑,我會親吻他的額頭,用我此生最溫柔的聲音,附在他耳邊跟他說,「爸爸,你到家了。」
「碰」的一聲,飛機真的著陸了,這是香港赤邋角機場。我的報紙,在降落的傾斜中散落一地。機艙仍在滑行,左前方那位老伯伯突然顫危危站了起來,我聽見空服員惱怒而凌厲的聲音:「坐下,坐下,你坐下!還沒到你急什麼!」
(2007/10/26 中國時報人間副刊 三少四壯集)